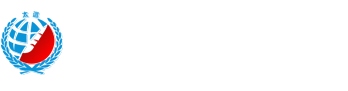成功案例
MORE>>在线咨询
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来源:admin 作者:admin 时间:2020-11-05
是指以非法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对于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来说,签订合同的着眼点不在于合同的履行,而在于对合同标的物或的不法占有,合同仅仅是诈骗利用的手段和形式。由此可见“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关键之一,但在司法实践中机关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如何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笔者认为,可以在对行为人事前、事中、事后各种主客观因素全面考察的情况下予以认定。
一、事前的履约能力
1、行为人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是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如行为人部分履行,但履行的目的旨在毁约或避免自身损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观原因造成或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的,也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2、行为人有部分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是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如其亦积极履行了合同,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也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但是如果行为人的履行意在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合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的,就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3、行为人无履约能力,而且之后仍无此种能力,却依然蒙蔽对方,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如事后经过各种努力,具备了履约能力,并且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则无论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构成民事欺诈。
二、事中的履行行为
履行行为的有无最能客观地反映行为人履行合同规定的的诚意。一般来说,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签订合同后,总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以后,根本没有去履行合同或者是虚假地履行合同。对于这种情形,不论其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如果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积极履行合同,但在尚未履行完毕时,产生了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意图,将对方财物占为己有,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履行行为虽然是积极的、真实的,但由于其非法占有的犯意产生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其先前的积极履行行为已不能对抗其后来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应构成合同诈骗罪。
在当事人只履行了部分合同的情况下,当事人对其占有的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很大程度就反映了其主观心理态度,即可以从行为人对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认定其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挥霍,或者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携款逃匿、隐匿财物且拒不返还等,应认定为行为人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观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之全部义务,一般不以合同诈骗罪论。
三、违约后的表现。
一般情况下,具有履行合同诚意的行为人,发现自己违约或者对方提出违约时,尽管从自身利益出发,可能提出辩解以减轻责任。但却不会逃避承担责任。当无可辩驳自己违约时,会有承担责任的表现。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纠纷发生后,大多采用潜逃等方式进行逃避,使对方无法挽回自己的损失。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对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债,或者在双方谈判时百般辩解否认违约的,不能一概认定为,应该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
一、问题及背景
从被取消的投机倒把罪名中分解衍生出的,第二百二十五条采用了叙明罪状表述,并以列举的方式作了具体规定。但是非法经营罪仍然保留了“口袋罪”的某些特征。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之规定,在尚无立法解释加以限制的情况下,显然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条款,从而给司法机关留下较大的自由裁量余地。
在修订刑法的过程中,对于取消投机倒把罪之后,是否需要在“非法经营罪”中留这么一个小“口袋”,曾有过争论。一种意见认为,由于新刑法要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规范的明确具体是罪刑法定的内在要求,因此,在新刑法分则中不宜再规定“其他”之类不确定的罪状内容,这也符合对“口袋罪”进行分解使之具体化的初衷。另一种意见认为,由于要取消类推制度,对“口袋罪”进行分解之后,如果对某些罪状规定得过于确定、具体而毫无弹性,对各种犯罪行为又难以尽列无遗,特别是在形态发展变化较快的经济变革时期,倘若有的条款一点“口袋”都不留,可能不利于及时打击花样翻新的经济犯罪,也不利于刑法典的相对稳定,因此有限制地设置一点“其他”之类的拾遗补漏条款还是必要的。新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正是更多地考虑了后一种意见而设置了第三项内容。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我国刑法改革的渐进性和传统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立法指导思想对修订刑法的深刻影响。
新刑法实施两年来,从司法实践的情况看,非法经营罪的“口袋罪‘遗传基因已经逐步显现。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之规定正越来越多地被援引,作为对刑法没有明文具体规定的有较大社会危害性的非法经营行为定罪的法律依据。由于”经营“的含义相当宽泛,生产、流通到交换、销售等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可能属于经营活动,因此,非法经营罪的适用范围在实践中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
但是,中国刑法毕竟已经步入罪刑法定的时代,灵活性必须以原则性为基础,任何与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刑事立法与司法都应当尽力避免。因此,如何理解和把握非法经营罪的本质特征,正确阐释和适用该罪条文第三项规定,防止非法经营罪任意膨胀成为新的“口袋罪”,从而动摇罪刑法定原则的根基,这是立法者、司法者和学者们应当共同关注的课题。
二、本罪的性质界定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只能适用于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非法经营行为。该条第三项的适用,也不能脱离这个基本前提。因此,对于刑法未明确规定的某种具有一定危害性的行为,若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上一篇:如何识别合同诈骗罪?
下一篇: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竞合适用